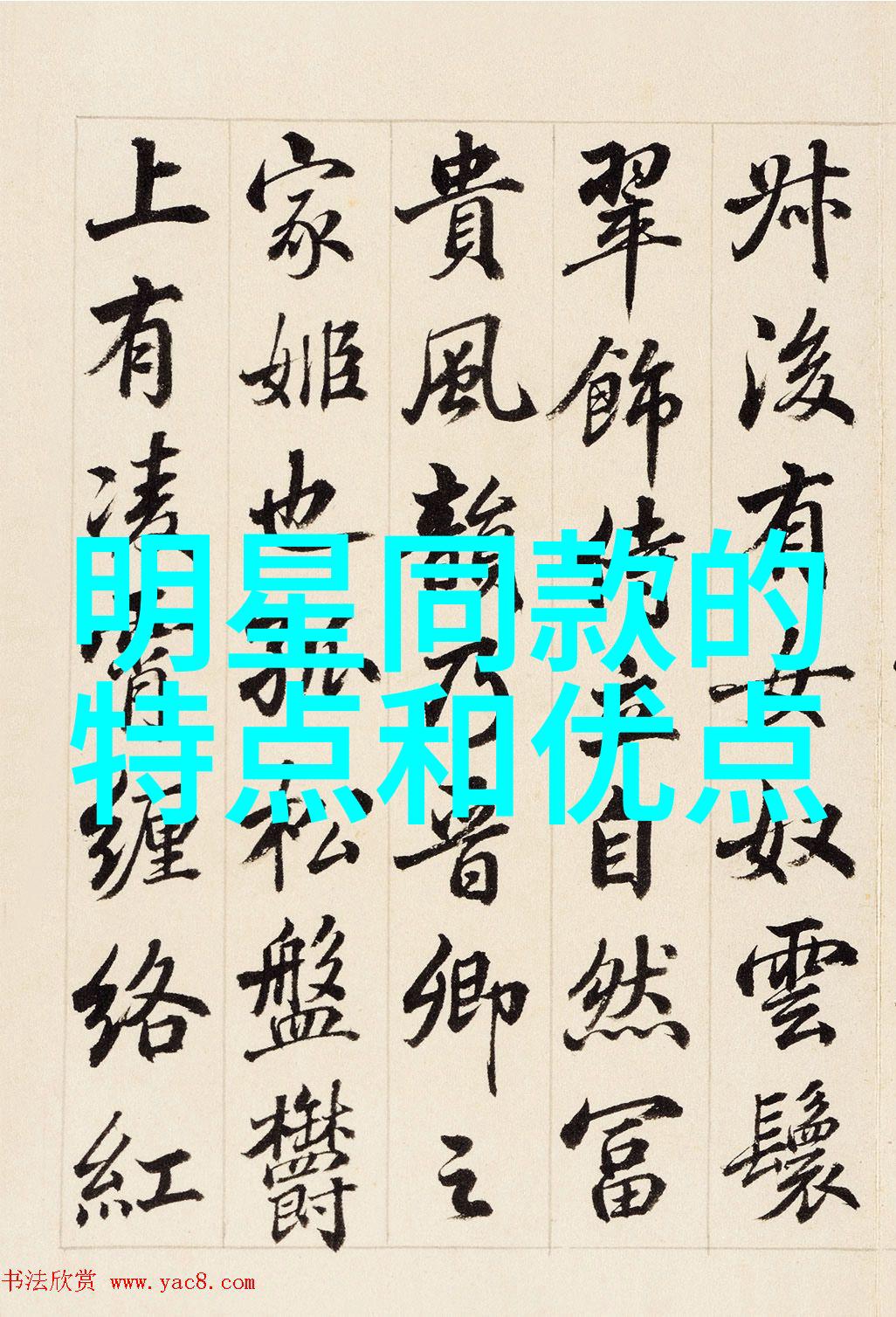《彼得罗夫的流感》中大胆的咒骂与狂放的镜头证明,外界压制并没限定基里尔的创作热情,他依然表达着愤怒和思考。

电影节作品往往存在观看门槛,很容易“看不懂”。
但这并不耽误作品仍是具有现实意义或者艺术价值的好片,比如:令受震撼的《彼得罗夫的流感》,就在戛纳电影节荣获了技术大奖。

本文有剧透。
1
彼得罗夫,一个普普通通的水管工。
可接下来几天的经历,却让他解锁了不属于自身生活的“新鲜”体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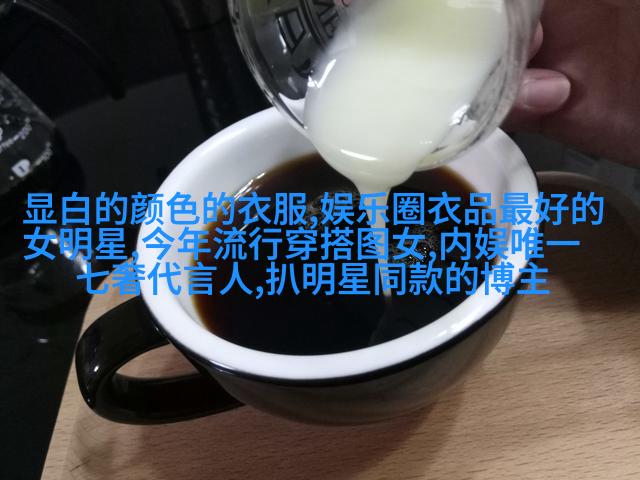
彼得罗夫正在公交车上被流感折磨,整个车厢里除了感冒的气音,就是人们此起彼伏的抱怨——缺少医疗福利、寡头高悬、移民问题激增、社会道德沦丧……

突然,公交车停下,彼得罗夫被一个手持武器的家伙带下车,并立刻递给他一把枪,还邀请彼得罗夫一起处决各个行业的寡头。

然而,枪声落幕,镜头一转,彼得罗夫又回到了公交车上。
原来,刚刚一切不过是他听到民众抱怨,开始在意识里脑补被口诛笔伐的掌权者走向末路。
可下一秒,彼得罗夫又被塞进了一辆装饰艳丽的灵车,人们仍在抱怨生活的不快乐,至于生和死只是体会悲伤的两种形态罢了。

另一边,身为图书管理员的彼得罗夫太太似乎也开始不对劲。
有一波自称诗社成员的人占用了图书馆的夜间时段,彼得罗夫太太只好在此加班,等他们离去再关门。
可听他们吟诵赞美的诗歌,彼得罗夫太太却突然开始旁若无人和丈夫,一套行云流水的操作下来,她也无比顺畅从朴素变得妖娆。

下一秒激怒她的,是一位常年借阅奇怪书籍的读者。
看他突然在图书馆惹是生非,彼得罗夫太太摘掉眼镜,瞳孔全部变黑,一把将其举过头顶,来了最血腥残忍的制裁。

回到家,眼前是只知道玩游戏却不学习的儿子,彼得罗夫太太内心的愤怒再次被燃起,她甚至想一刀杀掉儿子。

作为母亲的本能阻止了冲动,她只能到外面寻找新的泄愤目标。
这夫妻二人到底怎么了?
原来,他们都正经历一种难以自愈的流感,而误食过期阿司匹林,触发了种种诡异想象。
这些光怪陆离的念头当真只是一时冲动吗?
也许,俄罗斯的现实会给出比脑洞更加疯狂的答案。
2
《彼得罗夫的流感》注定不是一部善于同观众沟通的作品,尤其在不断跳跃的蒙太奇剪辑与伪一镜到底之下,有太多内容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但如果将其简化为从“患上流感”到“治愈流感”,似乎能够发现一丝解释作品内涵的端倪。
彼得罗夫一开篇就患上严重的流感,头晕目眩与想象力爆棚成了一种奇异的临床症状。
梦幻与现实交界,任由思维做主、超越物理空间的他,能够随意在各个场景穿梭,一会儿陪朋友去出版社被退稿,一会儿帮朋友完成成名前的大业,一会儿回到家给儿子绘制漫画。
不管彼得罗夫做什么,他都在与社会上的混乱发生关联,而体验过这场俄罗斯的都市冒险后,他仍然处于难以自愈的无助中。
同样处于流感漩涡的,还有彼得罗夫的儿子。
这个不听话的小男孩是妈妈眼中的问题儿童,但他和爸爸小时候一样感知不到现实社会的愤怒,即便因为流感发高烧也还期待着心心念念的新年派对。
所幸,过期的阿司匹林竟然让他退烧了,小男孩如约奔赴派对,成功治愈流感。
至于这条看似闲笔的“孩童胡闹记”,其实是与彼得罗夫的童年缠绕混剪,用现下的儿子对应当年的父亲。
他们都喜欢俄罗斯版圣诞老人“雪姑娘”,可三十年后的彼得罗夫却很难再被如此简单的快乐治愈。

况且,彼得罗夫不知道,当年治愈自己的那位雪姑娘,其实刚经历了背叛出轨并准备在这个不允许堕胎的国家铤而走险。
所有看似美好的东西,不过就是表面光鲜罢了,人人都有自己逃不过的绝望深渊。
最让人细思恐极的是,尽管电影里出现很多不同角色,但这些围绕彼得罗夫而来的人似乎都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行为动线,唯独彼得罗夫能够在真实与虚假中反复跳跃。
这意味着,其实每个角色都是他本人的意识投射。
彼得罗夫的幻想从未停止,《彼得罗夫的流感》就是一整个“人间大梦”,他才是这一切的唯一作者。

3
《彼得罗夫的流感》改编自阿列克谢·萨尔尼科夫的小说,原著曾在2018年获俄罗斯新文学大奖“鼻子奖”评论人奖,还位列2019俄罗斯国民级文学奖“大书奖”名单。
作者之所以选用“彼得罗夫”这个全俄罗斯最常见的姓氏作为主角名,就是为了借用后苏联时期一场流感影射当前弥漫社会的压抑与病态,尤其对应疫情,只要身处其中,无论多普通的人都逃不过。

但电影显然比小说更混乱,这也是导演基里尔·谢列布连尼科夫(《门徒》《盛夏》)常见的状态。
基里尔将大量镜头浓缩在狭小室内,以伪一镜到底来回晃荡,尽管动线有限,却凭借每个房间的不同设计,成功引导观众确信这些光怪陆离的意识流转,打造出一切混乱背后的末日感。
再加上节奏强烈、选取精当的配乐,与不同尺幅、色彩的画面完美契合,为彼得罗夫的想象铺设了恰当的背景。

贡献如此佳作的导演基里尔,其实并没到戛纳现场领奖。
他曾因挪用的指控被判软禁在家20个月,即便案件重审也没有获得离境自由。
很多人揣测,就是因为他发表和创作太多意识形态色彩鲜明的作品,才以这样的方式被长久留在俄罗斯。
不过,《彼得罗夫的流感》中大胆的咒骂与狂放的镜头证明,外界压制并没限定基里尔的创作热情,他依然表达着愤怒和思考。
儿子到父亲的角色互文,那片来自三十年前的阿司匹林便成了基里尔给出的解药——也许现代社会的弊病只能通过“回到过去”来治愈。
然而,当对过去的美好想象披上“”的外衣大行其道时,人们是否陷入一种更加难以名状的虚无和乏力?
也许,基里尔勇敢抗争的底色背后,才藏着更大的悲凉吧。